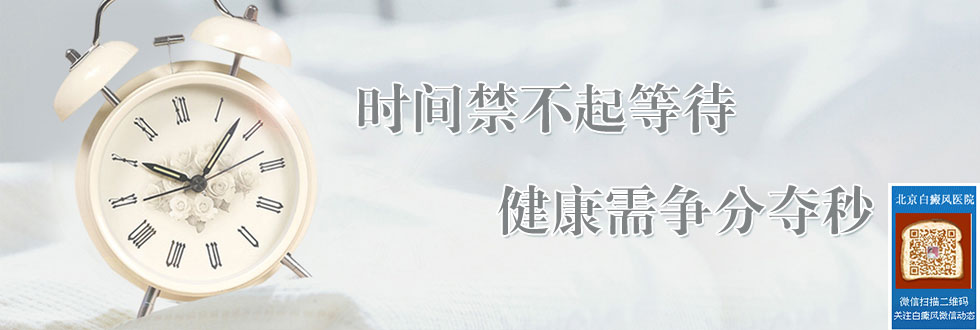郑某某,男,52岁,年10月16日初诊。
主诉:口中自感酸咸异味3月。
现病史:患者平素性情急躁。3月前不明原因出现口中异味,先咸后酸,时作时止,患者未予重视。近时上述症状发作,时刻不止,遂于今日求诊。辰下:口中异味,先咸后酸,心烦,纳呆,舌质淡苔薄黄稍腻,脉弦数而结。
处方:丹栀逍遥散加减。
当归9g白芍9g柴胡12g
茯苓15g白术9g薄荷6g(后入)
牡丹皮12g栀子9g牡蛎30g(先煎)
泽泻9g藿香12g佩兰12g
黄连6g砂仁6g(后入)谷麦芽各12g
7剂,水煎服,日1剂,分两次早晚饭后40分钟温服。
二诊(.11.13):患者诉药后先咸后酸明显减轻,一周发作2~3次,心烦已缓,饮食进步,眠差,余可,舌质淡苔白,脉弦数。效不更方,于上方去薄荷、泽泻、谷麦芽,茯苓改茯神,加炒枣仁、鳖甲宁心安神,牡丹皮、佩兰、藿香减量使用,处方如下:
当归9g白芍9g柴胡12g
茯神12g白术9g牡蛎30g(先煎)
牡丹皮9栀子9g鳖甲20g(先煎)
黄连6g藿香9g佩兰9g
炒枣仁15g砂仁6g(后入)
7剂,煎服法同前。
三诊(.12.4):患者诉药后口咸已止,自觉发酸,时有胃胀,多梦,皮肤瘙痒,舌质淡苔白,脉弦数。予上方加青陈皮各12、谷麦芽各12,白鲜皮20。续服14剂后患者口中酸咸未作,诸症悉除。
按语:《素问·六节藏象论》:“五味入口,藏于肠胃,味有所藏,以养五气,气和而生,津液相成,神乃自生”,指出了酸、苦、甘、辛、咸五味与机体生理病理之间相关,可反映脏腑的病变。从五味归属而言,酸味与肝对应,辛味与肺对应,苦味与心对应,咸味与肾对应,甘味与脾对应,正如《素问·宣明五气篇》所云:“酸入肝,辛入肺,苦入心,咸入肾,甘入脾。”故口味异常是脏腑病变的外候。
本案患者诉口中异味,先咸后酸,心烦,结合舌脉,四诊合参,乃肝郁脾虚,肾水上泛之征。“木曰曲直,曲直作酸”,患者素体性情急躁,肝气郁结化火,可见口酸、心烦;横逆犯脾,脾失健运,故见纳呆;清代张璐《张氏医通》云:“口咸,肾液上乘也。”肝木乃肾水之子,子病及母,且土克水,脾虚湿蕴,肾失气化,失于封藏,肾水上犯于口,则见口咸。
针对上述病机,吾师治以疏肝健脾养血,清肝泻火利湿,汤方疏以丹栀逍遥散加减,以调肝脾为主,肝脾调和则肾水自平。方中以当归、白芍、柴胡养血柔肝,疏肝解郁,一柔一疏,与肝体阴而用阳的生理特性相符合;茯苓、白术补气健脾,渗利水湿,脾土健,兼能制约肾水;薄荷透达肝气,助柴胡以疏肝;肝郁化火,故佐以牡丹皮、栀子清肝泻火;牡蛎潜阳,兼能宁心安神;泽泻功专利水渗湿,合茯苓、牡丹皮乃取六味地黄丸中三泻之意,可泻肾浊,助真阴得复其位;肝郁横逆犯脾,脾失健脾,湿浊内生,除健脾外,尚需芳化醒脾化湿,故辅以藿香、佩兰、砂仁醒脾芳香化湿;湿浊内蕴化热,黄连清热燥湿,兼可助栀子清热泻火;砂仁兼制黄连苦寒之性以防伤胃;谷麦芽消食和胃,运转脾机。
二诊患者诉口中酸碱较前明显减轻,心烦亦缓,饮食进步,眠差,故于前方去薄荷、泽泻、谷麦芽,茯苓改茯神,加炒枣仁、鳖甲以养肝宁心安神,藿香、佩兰减量使用防其温燥,牡丹皮减量以清热泻火。
三诊患者诉药后口咸已止,自觉发酸,胃胀,皮肤瘙痒,效不更方,中药守上方加谷麦芽、青陈皮以消食和胃,理气健脾,白鲜皮祛风除湿止痒。续进14剂后诸症悉除。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